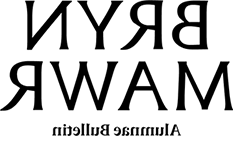移民与归属
一位住在哥斯达黎加的印度裔美国妇女探索了离开并找到家的冲动.
1959年7月, 我的母亲Saroja第一次登上飞机, 正从南印度前往纽约. 这次旅行花了三天时间. 她23岁,从未独自生活过.
离开印度纯属偶然. 就在医学院毕业之前, 一位同学告诉她有一个让外国医生来美国工作的项目.S. 由于在印度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什么工作前景,她申请也没什么损失. 这个不切实际的决定让她来到布鲁克林的一家医院,成为一名儿科医生.
1965年以前,.S. 移民法的设计将非欧洲人排除在外, 所以Saroja(见下图)是一名持有五年签证的外来工.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遇到并嫁给了我的父亲,他也是一名印度医生,并生下了我. 当他们的签证在1964年到期时,他们在新斯科舍省的一家教学医院找到了工作. 但是和美国一样.S.在美国,加拿大移民政策优先考虑欧洲人. 当我母亲申请一个高级职位时, 儿科主任告诉她:“你有背景, Saroja, 但我们得把这份工作给一个养家的加拿大男孩.由于前途渺茫,他们决定于1969年返回印度.
在印度,他们的北美培训和董事会认证以及我父亲的美国博士学位.D. 毫无价值,所以他们以初级医生的身份重新开始. 工作不稳定,工资低. 他们申请移民到美国.S. 根据新的法律. 三年后,他们的申请被接受了. 就这样,在我9岁的时候,我作为一个移民来到了我出生的国家纽约.
在这样一个漂泊不定的童年,我似乎会在某个地方扎下根来. 然而,我现在是第五次移民,也是第八个居住国——哥斯达黎加. 我的人权工作使我在许多国家做过短期和长期停留. 当我访问美国时.S.在美国,我陶醉于见到家人和朋友,但在那里我也是一个局外人.
我的新家以原始的海滩和热带雨林而闻名, 但哥斯达黎加也是拉丁美洲外国出生居民比例最高的国家. 绝大多数来自尼加拉瓜, 与委内瑞拉人, 哥伦比亚人, 萨尔瓦多人, 和海地人, 等.
尼加拉瓜人多年来一直来到繁荣和稳定的哥斯达黎加. 他们从事哥斯达黎加人认为过于繁重的工作:采摘咖啡, 建设, 食品加工及, 尤其是对女性来说, 清洁及家务工作. In 2018, 尼加拉瓜的残酷镇压导致一波持不同政见者加入已经在这里工作的尼加拉瓜人的行列. 2020年之后, 这些不同的尼加拉瓜移民浪潮在哥斯达黎加面临大流行病的同时,不得不支持国内处于绝望境地的家庭.
“当我问人们是否能认出她是尼加拉瓜人时, 她指着自己的胳膊笑了, “Soy morena”(我皮肤黝黑).'"
看到疫情期间护理工作被低估的情况,激发了我对在哥斯达黎加从事家政工作的尼加拉瓜移民妇女的研究. 我一直在采访尼加拉瓜妇女,以了解她们是如何养家糊口和照顾自己的. 我在海滩上遇到了妮莉亚,她是一家旅馆的女管家. 当我问人们是否能认出她是尼加拉瓜人时, 她指着自己的胳膊笑了, “Soy morena”(我皮肤黝黑). 在我这个外国人眼里,她看起来和哥斯达黎加本地人没什么不同. 我瞥了一眼自己的手臂,比起她的金棕色,我的手臂更黑了. 妮莉亚谈到了她的孩子们在学校被单独挑出来欺负,被称为“Nicas”.然而,她和她的孩子们在哥斯达黎加都比在尼加拉瓜有更好的前景. 这里的平均收入是尼加拉瓜的两倍多,而且来哥斯达黎加而不是美国.S. 避免了语言障碍和危险的北上之旅.
在大流行期间,哥斯达黎加的一些政客将犯罪和疾病归咎于“nicas”.“故事更加错综复杂, 由于生活和工作环境拥挤,COVID-19对尼加拉瓜人的影响更大.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替罪羊. 2020年4月, 副总统埃普西·坎贝尔·巴尔分享了她与持突击步枪的移民官员在尼加拉瓜边境的照片, 标题是:“我们在这里做的是保护自己 ... 住在我们国家的人.她的信息清楚地将尼加拉瓜人“视为”危险的罪犯.
研究表明,尼加拉瓜移民对哥斯达黎加人的就业和工资作出了不成比例的贡献, 尤其是技艺高超的哥斯达黎加妇女. 在一个家庭性别分工严重、缺乏机构托儿选择的国家, 没有尼加拉瓜雇主,很少有哥斯达黎加妇女能够外出工作. 生育率为1.8、换人不足,哥斯达黎加需要劳动力. 但是和美国一样.S. 在欧洲,妖魔化移民可以让政客们转移公众对他们自身失败的注意力.
看起来像印度人,说西班牙语,这让我成为了一个外来的好奇, 既不被视为来自贫穷国家的移民,也不被视为“外国佬”或典型的美国人.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世界正在目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人们从乌克兰战争中逃离,加入委内瑞拉的人流, 叙利亚, 阿富汗, 还有很多其他地方. 与人类运动相关的全球建筑和法律是二战后和冷战时期的遗迹,当时“政治”和“经济”移民更容易分开, “自愿”和“非自愿”也是如此.“在一个人们逃离各种自然灾害的世界里, 战争, 气候变化, 和贫困, 这些区别并不那么明显.
有时,我采访的尼加拉瓜妇女看到我这么小就会笑, 对我说:“我们一起去吧。!-你长得像我们. 但相似之处就到此为止了. 我是带着第一世界公民的特权来到哥斯达黎加的. 看起来像印度人,说西班牙语,这让我成为了一个外来的好奇, 既不被视为来自贫穷国家的移民,也不被视为“外国佬”或典型的美国人. 我的外表让我可以在自己的类别中浮动.
我的流动便利来自于我父母坚持不懈的移民. 我不是在逃避政治压迫、气候变化和战争的影响. 虽然我理解离开和重新开始的孤独感和心理需求, 精英教育和选择学校的自由为我的经历提供了缓冲. 然而,我被我采访的移民所吸引, 了解再造的过程,以及离开熟悉的一切并进行改造的冲动.